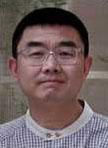
张永和,男,当代著名建筑师,非常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美国注册建筑师;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建筑系硕士;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负责人、教授;2002年美国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丹下健三教授教席;2005年9月就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建筑系主任。 所获荣誉列表: 设计特点:美国进步建筑奖1996 作为8名中国建筑家之一入选日本《世界之建筑家581人》1994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Steedman建筑旅行研究奖金(去欧洲、亚洲考察一学年)1992-93 美国纽约建筑联盟:青年建筑师论坛奖1992 美国建筑师协会旧金山分会/旧金山建筑基金会:旧金山洛杉矶3X3+9设计竞赛获胜者1991 日本新建筑国际住宅设计竞赛佳作奖1991 美国密西根大学:Walter B. Sanders设计教学研究奖金1988-89 美国"从桌子到桌景"概念性物体设计竞赛一等奖1988 日本新建筑国际住宅设计竞赛一等奖1986 美国建筑师协会印地安那波利斯分会"纸上建筑"竞赛荣誉奖1986 美国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Bakewell & Brown和Bakewell & Weihe建筑画奖1984 美国建筑师协会/基金会奖学金1983-84 美国金钥匙荣誉协会终身会员1982 张永和1977年考入原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建筑系。
1981年赴美自费留学。先后在美国保尔州立大学和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建筑系分别获得环境设计理学士和建筑硕士学位。在校时获得美国建筑师协会和基金会奖金。
1984年毕业后曾在美国旧金山几家建筑设计事务所工作。1985年开始相继在美国保尔州立大学、密执安大学、伯克利加大和莱斯大学教书。其间曾在一系列国际建筑设计竞赛中获奖,如1986年荣获日本新建筑国际住宅设计竞赛一等奖第一名。
1988年荣获美国福麦卡公司主办的"从桌子到桌景"概念性物体设计竞赛第一名。1988年荣获美国密执安大学W.桑得斯建筑设计教学研究奖金。
1991年参加美国建筑师协会旧金山分会/旧金山建筑基金会主办的旧金山/洛杉矶3X3+9设计竞赛,获优胜奖。同年,以"垂直玻璃宅"获日本新建筑国际住宅设计竞赛佳作奖。
1992年,获得美国纽约建筑联盟青年建筑师论坛奖,在纽约举办作品展并发表演讲,同年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史戴得曼建筑旅行研究金大奖。
1989年成为美国注册建筑师。
自1993年起,与鲁力佳成立非常建筑工作室并开始在国内的实践。
1996年底正式辞去美国莱斯大学教职,回国。自1992年开始,由他设计的洛阳老城幼儿园、郑州小赵寨住宅区及幼儿园、汕头华利迪娱乐城、清溪山地住宅和虎门政府花园式酒店等工程相继发表在国内外杂志上。1994年作为八位中国建筑师之一入选日本《世界上581名建筑家》一书。1995年,在广东清溪的"坡地住宅群"工程荣获美国"进步建筑"1996年度优秀建筑工程设计奖。(进步建筑奖为美国建筑界最权威的建筑年度奖之一,这是首次中国人设计的在中国的工程获得此奖。)1996年完成北京、南昌、武汉的席殊书屋等室内设计工程。1997年完成北京美国康明斯公司"颠倒办公室"工程、深圳润唐山庄住宅小区工程, 1998至1999年完成广东清溪坡地住宅群、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楼工程、北京现代城样板间室内设计工程、北京怀柔山语间住宅工程、北京玻璃洋葱餐馆、北京红石实业办公室室内、北京水晶石电脑图像公司外立面及室内设计,河北燕郊画家工作室/住宅7#、4#、5#、3#工程,2000年完成重庆中试基地等工程。 自1992年起多次参加亚洲、欧洲、美洲等地举办的国际建筑及艺术展,其中主要包括:2000年上海双年展,并获得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艺术贡献奖(表彰在视觉艺术领域突出和有创造性成就);作为唯一的中国建筑师参加2000年在威尼斯举办的第七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1999年在美国纽约Apex Art艺术画廊举办个展"路边剧场";97-98年陆续在奥地利维也纳、美国纽约PS1、丹麦路易斯安那现代美术馆、英国伦敦等地举办的"运动中的城市"中参展并完成部分展览设计;1999年参加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的国际建筑师协会第20届大会中国青年建筑师作品展;英国伦敦AA建筑学院"可大可小-亚洲建筑三人展";97年在日本大阪、98年在印度举办的"亚洲进步建筑"展及'97韩国光州艺术双年展等。 1997年出版《非常建筑》作品专集,2000年出版《张永和/非常建筑工作室专集1、2》。在国内的学术刊物上多次发表学术文章,并先后在法国的《今日建筑》,意大利的《瞬间艺术》,日本的《新建筑》,《空间设计》,西班牙的2G,美国的《进步建筑》及《建筑》,韩国的《空间》,《韩国建筑师》,英国的《世界建筑》,《AA档案》等杂志及美国的《慢空间》一书中发表作品及文章。 八步走向非常建筑(朱涛):http://www.aaart.com.cn/cn/bbs/dispbbs.asp?boardid=3&id=360 对张永和的访谈——有关“非常建筑”十年与中国建筑非常十年 成婴/采访(《财经时报》) 中国建筑实践、北京城市面貌 ஸஸ成: 十年间,中国作为一个大工地给中国建筑师提供了很多建筑实践机会,是不是有种急战练兵的感觉?您主持大陆最早的私营建筑设计机构之一——“非常建筑工作室”,披风逆雨参与实践,请问您有何感受? ஸஸ张: 急战练兵就是没准备好的意思是吧……我自己是真的完全没有准备,原来在美国,我在学校里教书,没想到会一下有这么一个大规模的实践机会。可是我觉得,本来就在中国的建筑师也不见得准备得多么好。而且这准备一定是两方面的:一个是技术上的准备,就是从事务所组织到真正对材料、结构等等的熟悉程度,还有一个就是态度上的准备。这些机会来了到底怎么利用,好像都没有太清楚。惟一的,大家好像也是把它看得跟其他机会完全一样,把它看成市场经济的一个机会。我自己的情况是特别差了,是挺可笑的,一开始我做了那么一段时间,没想到会那么难多问题,那时候还在美国中国两边跑,回到美国跟美国以前的同行说,中国啊怎么怎么样,中国怎么怎么样,(笑)他们说其实美国也一样,在美国实践也有同样的困难,只是那会儿你没做所以你不知道。所以实际上,现在说有十年了,实践都是在这十年里慢慢地通过好多好多的教训学到的。 ஸஸ成: 一个建筑往往是由很多个专业群体和职业团队运用参差的理解力和行动力共同创作出来,在中国也不例外,您是否认同——无论最终形成的是怎样的建筑设计作品,其实都包含着设计者一定的倾向(某个时期的审美甚至是某种价值取向)?您是否认为建筑师一旦以健康、积极的态度开展工作,无论是在怎样复杂的情况下,也一定能达到某种成效? 张: 建筑师自己的审美习惯常常能在建筑里反映出来,可我也不认为它这么重要。一个房子的粉刷如果让我设计,按照我的审美倾向,我几乎就一定会设计成灰的,业主可能给设计成红的了,如果空间结构还都是一样,到今天我就不会认为还是很大的问题,也不是因为我本来也可以喜欢红的,而是因为建筑本质的东西没变。 ஸஸ在香港我看见一个公园,公园两米高的围墙,上面都是琉璃,绿的,公园的门像个牌楼,里面的树木特别特别的茂盛。我现在看就一点儿也不觉得别扭了,觉得老百姓对周围有这么茂盛的树木会挺喜欢的。可是我也明白,如果这公园的围墙交我设计,我还是不会这么设计。你看见没有,在态度上我是开放的,我可以接受很多东西,因为我能判断什么更重要。可要是没有什么人非要跟我较劲,我显然也不会违背我自己的趣味,而趣味我认为整个的又并不多么重要。当然不管条件多复杂多困难,一定是能达到某种成效的。成效是什么?不是视觉效果,而是你要追求的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像我们在石排的房子,最重要的就是良好的通风、遮阳,降低室内温度,主要就是一个舒适,这不是应该很好理解的吗?可当时的人就是不理解,他们都是用空调,业主反而比建筑师还不实用,他们总想这房子一定要是什么什么样子,用空调也没关系。我们的设计他们一会儿觉得像工厂,一会觉得像大菜棚,反正他们觉得这个都比房子好用重要。当然现在房子真使上了,他们就发现房子好用还是挺重要的。那个项目我们主要想达到的“成效”,就是要达到非常好的自然通风、遮阳,实际上我们想要一个真正的南方建筑,为此,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而房子盖之前,有百分之九十八的镇上人都反对,现在反过来了,大多数镇上人都喜欢。这房子在审美上看,不会觉得房子有意思,不知道我们功夫下在哪儿,可使用的人很开心,我们也很开心。你没看到我说的那个房子呵,我指给你看:向南有大的柱廊,这房子特别薄,里头交通空间跟室外都是通着的,是拔风的自然地通风的。这房子我们开始设计的是灰的,被新上任的镇长改成白的了(笑),可实际上我觉得也没关系,还有你看这个(楼侧挂着大排大串的红灯笼),以前我觉得跟我们的房子是特矛盾呵,现在我也不觉得了。我在这房子门前参加了一个开幕式,要人都讲了话,还表演了耍狮子、中学的鼓号队、军队的军乐队等,所有的活动,介绍人还放彩炮,炮打出来的都是彩色小纸条,前后一共就二十分钟,就这么一个活动,组织得真棒,当时我的感觉就是我们这个房子能有这么一个活动,其实有它的理由,作背景,感觉就特别的好,实际上这房子是可能被这么用的,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ஸஸ有一方面我挺有感触的,有一些朋友,大概是1996年在我们家聚会认识的,当时大家发言、说话,艺术家们就讲他们感兴趣的是什么,建筑师只是抱怨,抱怨业主、政府官员、建造环境、施工质量,全都抱怨到了。可是你看如今那天在六箱建筑研讨会上,就已经没有人抱怨了,这还是变化了,现在的条件其实也未必比六七年前的条件有多少改善,是建筑师的态度改善了。人都是会老的,年轻的时候如果都是抱怨度过的,老了会后悔啊。 ஸஸ成: 请您用一些词汇评价一下北京的当代建筑,您能告诉我们从一个有建筑修养的人看来,北京哪些区域的城市建筑面貌是打动您的,您欣赏的设计作品有哪些? ஸஸ张: 评价北京,这个问题就麻烦了,(当代建筑打动我的)说实话就是没有,老北京呢有很多。很多的街正在被破坏,像南长安街多好,南池子这些街多好,国子监啊……多了。现在不行了。你看我现在住的地方,还有圆明园(非常建筑工作室办公地点)、镜春园(北大建筑研究中心办公地点),我真心地最满意的一点是在我工作、生活的地方,那里我见不着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房子。六十年代以后的房子,它或许好看点或许难看点,可它跟城市真正的生活质量一点关系都没有。当然很多房子在趣味上好像就怕自己不够恶俗似的。(我喜欢的)老房子那就多了:儿童医院,包括以前的农科院、同仁医院……多了,多了。都是六十年代往前,包括三里河被扒掉的三里河小区。刚才说的有赵冬日设计的,有华揽洪设计的,还有日本人设计的。我觉得北京城市面貌杂乱无章。我觉得“千篇一律”实际上很重要,可是那“律”是什么,得说清楚。房子当然应该都一样高,不该高低错落的,当然都应该一样的颜色了,不应该那么花花绿绿的,那样城市看上去跟居住需要的安静还能挂点钩吗。 自私想法 成: 设想一种良好的国家政府职能,建筑师应更好更多地参与城市的规划设计。如果让您选择,在建筑师、甲方、政府官员(对设计方案有前提决定权或最终决定权)三位之间做选择,您是…… ஸஸ张: 这其实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显然我很喜欢建筑,要是从这三个里边选呢,我还是会选建筑师。可我也特别不适合做建筑师,我其实没有组织能力,我不太能与不同的人打交道,在我这儿是属于阴错阳差的一个事儿。跟人打交道我为难,觉得挺怵的,也不是很喜欢。但是这三个中呢,我还是选择建筑师,因为我的确感兴趣。可是建筑这行当啊,对我来说实在是有点费劲。这个职业对我来说挑战真是太大了,而不是有一点。在中国,做建筑的一些人比较多的起点大概都是写写画画,可是很多人,因为建筑师工作的社会性嘛,他后来就很有这方面的能力,包括组织、经营啊,只不过在学校里还没有太多发挥、体现出来。我呢,属于真上阵要用的时候是没有,实在是没有,很痛苦。其实教书对我来说啊,是能胜任的。 ஸஸ教学是很特殊一种情况,人家本来就来听你说的嘛,教学一说五六个钟头根本没问题,其他就太难了。而且我脾气特别不好,我有时候跟业主急。外交里其实不是你说了怎么想就能解决问题,我基本是怎么想怎么说,这本身就是个问题。一急更是谁都一样了。对一个半懂不懂的业主我会急。人会觉得我胆儿大,其实根本不是胆大,这方面我是不够理性。业主真要不懂,我倒不会急。跟同事也反而不太会发脾气。我们公司里的气氛也不像别的公司。有一点我是有自信的,我自己有民主观念,不是体制的民主,是个人对民主的理解:第一是独立思考,第二是互相尊重。可我不尊重无知,如果他要炫耀的话。 ஸஸ我最幸福的一天就是不用出去,不用见人,在圆明园,在自己窝里做一天事,就挺高兴的。怕开会呀。学校里学术活动也挺多,建筑师之间有些来往。我的朋友里建筑师并不多,五花八门的什么都有。(我也并不是就喜欢搞艺术的,行当对我来说不是有意思的事,但人有意思。 ஸஸ成: 现在是个观念满天飞的时代,您曾经说到,建筑师是通过设计为社会服务的,一个人如果必定要用一种职业来介入现实世界,为社会服务,建筑师是您的最佳选择吗? ஸஸ张: 在北京,概念什么的主要是房地产宣传上说一些挺不着边的事儿。说到选择一个职业,其实是有一个矛盾的。从我个人来说呢,其实未必一定要介入到现实社会,另一方面也不一定非要做建筑师。我并不是首先想到要为社会服务,再做建筑师,正好相反,因为是做了建筑师我才意识到要为社会服务,建筑跟人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否则我理想的一个工作——如果不考虑对别人是怎么影响的,就是自己一个人写写画画,要说怎么生存,就是通过教书了,这些都是比较能够把握的。其实现在当建筑师这档子事,跟社会这么打交道,这么复杂的合作,全都不是我擅长的。问题是我喜欢盖房子,其实我对建筑的理解特别简单,就是感兴趣盖房子。做学者又不是我的兴趣,我那写写画画完全不是指传统研究,比如历史研究理论,要说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写侦探小说,我想试着写一个特别短篇的侦探小说。可能,看看吧。 ஸஸ我觉得容易引起误解的,也是我最幸运的一件事,就是一般常人有的名利心我都有,但是又真的不是很重,真的只是兴趣出发,这一点人家很难想象。现在很多人都是有很明确的奋斗目标,然后就苦干,像我就没有,我根本就没想到。最没想到的就是非常建筑还能干十年,十年以后还能叫“非常建筑”,你知道当时根本没有长期的计划。就工作室模式的实践,我看我的老师是这样,我老师的老师也是这样,我同事是这样,我的同学是这样,我自然就觉得做建筑就该这么做。今天要这么说可能有点没劲,可真的当时要知道做建筑这么难,没准我就留美国教书了,当然也不后悔。要一开始知道这么难可能很容易就被吓回去,也幸亏不知道这么难,要不哪还自己办公司。一个历史的机会促成了现在的情况,真的不是个人能够预料、能够计划的。咱也不后悔就是了。 ஸஸ我觉得人有兴趣是特幸运的一个事,像做工程,一个接一个地做,可再有意思的事,没有兴趣也早没意思了。我喜欢吃炸酱面,早饭一顿,中饭一顿,晚上一顿,一天三顿没问题。夜宵再来一碗,也还行,反正喜欢吃。但半夜被叫起来,已经吃了四顿炸酱面,还得再来一碗,嘿,你看,这得多喜欢炸酱面才能再吃啊。 ஸஸ成: 人们有时会处在一种特别的两难境地:是费神使兴趣投入之处全面开花,还是让自己更为俭省专注,只将精力集中在特定的一两件事情上。您身兼设计、教学、研究以及艺术活动策划等多重角色,它们各自的份量都很重,十年间,哪些方面的大胆设想和实践取得的成果较为令您满意? ஸஸ张: 这也是挺矛盾的一件事情,像我这个能力,最好是集中精力在一两件事情上。可现在的机会是挺难得的,就像北大研究中心这事,我在美国因为教了十来年书,老想要是有一个机会办学那多好,教育想法可以贯彻。回中国来后是在最忙乱的时候这个机会来了,于是不忍放弃,也就给招呼两把,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其实心也不一定有余,力也更不足,现在从工程的量上也很贪婪似的,可是另一方面你也不知道哪个工程真的是能做起来的,要是事先都知道就可以有选择了。现在工程做得比较多。 ஸஸ艺术的事,一开始本来是个分心的事、挺轻松的事,后来越做越认真,越做越多,也就不轻松了。这真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这些机会和自己的能力……不知道怎么好,累得是死去活来。我和鲁力佳都觉得,要不干真是一点儿也不难受,干了干不好反而难受。不想干的时候,往往挺好的机会又来了,这样折腾来折腾去,就到现在了。 ஸஸ看起来我很精力充沛,可我没生活呀,我现在不聊天。我跟你说实话,因为我现在整天谈这个,全都是说话,我确实不喜欢聊天,偶尔见到朋友挺高兴的也不想说话,就看看。确实不喜欢谈建筑,谈建筑我并不觉得放松,尽管我喜欢,因为陷得太深。我总问别人能不能谈点别的,谈点电影、服装什么,不过现在电影也没时间看,如果有时间也看不了,太累了,看十分钟就不行了。 ஸஸ成: 无论哪一方面的实践,恐怕都存在现实的栅栏和想象的野马,您如何处理它们的共同存在?一般来说,您为难的是怎样围栏养马,还是怎样去搭建一个更大的空间让它们各得其所?请随便说说您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吧。 ஸஸ张: 你看呵,我们做出来的东西看起来还有点艺术性,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野。实际上我们的工作特别理性,会仔细分析方方面面的条件,正因为分析了,不会用一个简单的现成的答案,就让大家觉得这个答案有点新鲜,好像比较有想象力似的。正是现实中的问题会让我们做比较深入的研究,一些限制反而会启发想象力,而且就跟前头讲的,实际上这不是建筑设计的问题,而是建筑设计的特点。 ஸஸ我自己,比较自私的事儿就是写东西。我写东西抱的态度跟我盖房子很不一样,我写东西真是自娱的成份特别厉害,所以人家会看不懂。我也还是喜欢文字,里头有些乱七八糟的,一方面可以说我写东西特别真实,反映我的思考和兴趣;另一方面对于外头人来说,是进入的可能性特小。最近新写的是《浮出空间》。我几年前写东西的时候,有的人说玄啊,莫名其妙啊,五六年前写的东西现在人都看得懂了,可我现在写的东西人家又看不懂了,是不是还得等些年? ஸஸ侦探小说我多少年前就想写了,这个小小的梦想不知道怎么实现。现在,年关还过不了呢(房间那头,仍在工作的鲁力佳笑说:“张永和有时特别疯狂,在特别疯狂工作状态的时候还一整晚一整晚地写。”)现在写的一些文章,当然不是文学的,是我自己的书,东京办展览的书里有要写的,十年专辑里有要写的,《32》杂志里我翻译自己的东西也答应了别人。一般建筑师做完了工程就没事了,我们做完了还出书,做交流工作。此时此刻,我和鲁力佳其实是什么都不想干,要是有一年能什么都不干多幸福呀。实在累得太狠了。(未完待续)建筑师、交流传统、建筑评论 ஸஸ成: 库哈斯关于城市规划的理论强调“城市历史的连续性”和对“城市生活”的关注,您对他在北京创作的“板凳”(CCTV电视台新址)怎么看? ஸஸ张: 库哈斯电视台的设计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能够反映他思想的例子。在北京,这是一个孤零零的房子,特别是这个房子是用传统的围院的方法围起来的,他也没什么办法。他所想象的历史的连续性,实际上在一个建筑里是不可能实现的,那里三环边一堆工厂将来是否能保存啊什么的,恐怕都不是建筑师能够控制的。而“对城市生活的关注”,其实是北京的问题,不是那块基地,具体这个项目的问题。 ஸஸ成: 据您察觉,在中国,建筑师和公众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他们之间的交流是否不同于现在的西方发达国家,您对此怎么看? ஸஸ张: 在美国和欧洲,所谓发达国家,也挺不一样的。在欧洲,设计文化比较发达,媒体也比较多,年轻人主要指大学生,对设计师、建筑师,对哪个房子是谁设计的都比较熟悉。美国不行,在美国我好几次发现知识分子有些甚至在纽约的,不知道斯蒂文•霍尔是谁,斯蒂文•霍尔在建筑圈里的国际声誉是仅次于弗兰克•盖里的,可是他们不知道。 ஸஸ在中国,恐怕公众也知道得非常少。可是好像又不是那么少,连开发商也知道请外国建筑师来做做广告。这一阵子,光这些电视台、奥林匹克广场啊也或多或少给公众介绍了一些建筑师的概念。文革以前其实是没有建筑师的说法,都叫工程师。现在有时候叫建筑师,有时候叫设计师,这是两个极端。叫设计师好像把建筑师想得很艺术,以前叫工程师当然就很技术,实际上建筑师真正的工作公众很不了解。建筑师跟公众发生的关系一般就两个层次吧,一个是通过设计的房子,另一个就是通过媒体。可是我们现在的报纸由于极端的市场经济,都有房地产版,却很少看到建筑版。而《纽约时报》会有建筑版而不会有房地产版。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差异,我们现在谈建筑,常常放到一个房地产的环境里谈,而《纽约时报》是放到文化那一块谈的。 ஸஸ成: 针对当代中国的建筑设计状况,您认为建筑师存在的普遍不足和相对来说较为集中的难能可贵之处分别有哪些? 张: 问题我看得比较清楚,难能可贵的都已经被库哈斯说了,就是“量”。最大的问题就是对建筑、建造本身的不关心、不熟悉。现在建筑师比较熟的还是里外两层皮,消极地知道结构是八米柱距等等,在结构、建造、围护方面的创新,因为研究能力和态度问题等等就特别少能看见。结构都是很消极的,围护都是藏在里面的,真正建筑最核心的那部分,建筑师反而参与得少。 ஸஸ成: 看到您在一些文章中冷静讲述自己在电影、文学、美术、装置等艺术门类中对建筑意识的表达进行的观察,您是否建议建筑系学生、建筑师也多从这些观察中思考,得到收获。反正这让我很有点好奇,您负责的北大建筑学研究中心进行的建筑学教育有哪些不同于一般建筑学院校的地方? ஸஸ张: 这个问题有两方面,一方面我并不认为一个学建筑的人一定要兴趣很广泛,虽然我是这种情况;另一方面,在教学里,我们的主课是没有这些东西的,一些属于讨论性的研讨课就可以有一些跨学科的、边缘的。这学期我们请了王军、龙应台,下学期一开学我们就邀请德国导演温德斯来讲电影,我们的课还得回到主题来,是“电影与建筑”,都属于北大建筑研究中心的讲演系列,是对全北大开放的。 ஸஸ成: 看您对自己设计作品的诠释,感觉您胸中有观念,但更多来源于一种诗意。也许这正是您的作品容易引起争论的原因。您对中国当前的建筑批评怎么看? ஸஸ张: 因为我们比较理性,所以很多地方可以谈出是怎么想的,而不说“觉得”怎么样,当然就出来一个问题,很多人难以理解。在中国,人们习惯于把感性和理性分得比较开,要感性、诗意的艺术似乎就得喝点酒才能狂起来,我不认为艺术和诗意是这样。有两种情况,有的人认为我们的房子干巴巴的,还有部分人不相信我们有理性的开端,不认为我们讨论的建筑师的理性思考就是引导我们去发现建筑的诗意的东西。 ஸஸ现代艺术的鼻祖像杜尚,我特受影响,都是非常理性地有逻辑地去观察一些问题,然后在理性里最后推导出诗意、甚至是非理性,我一直对这个感兴趣。可以说中国建筑界对西方现代美术思潮不是很熟悉,现在谈的一种诗意和艺术还是传统的,激情四溢的,跟我说的“冷静的诗意”差得比较远。 ஸஸ还有一个问题,到底建筑与美术有多大关系,我根本不认为学建筑就应该学画画,可是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应该有美术修养,建筑师当然是,所以我认为一个建筑系学生应该上大量的美术赏析课,多看,而不在于自己画得多好,是否画画。 ஸஸ现在的批评呢,我看也是缺乏理性,还是原来中国文人的那套,特虚。我们觉得那是很主观的,是很不能引起积极讨论的评判方式。在中国,大师情结比西方建筑师不知厉害多少,可根本不是这问题。干一辈子,如果能出几个好房子,当然就有可能当大师,但这不太能够作为目标追求。 成: 在建筑师同行中,您目前较为关注的设计实践有哪些?身处“在急速翻卷的市场浪潮中急速狂奔的中国建筑界”,现阶段,您与您了解的国外建筑师同行们所做的实践有什么不同吗? 张: 中国建筑师与外国建筑师不一样的地方挺多,一个美国建筑师的愿望在中国建筑师里可能没有也很难做到,就是自己设计房子自己盖,完全靠自己动手。我们北大研究中心很受美国这种建筑文化影响。刚才谈到垂直向的两代建筑师的继承问题,还有水平向的同代建筑师的切磋,人家时间上比咱们从容多了,很多不一样。咱们中国建筑师常常羡慕外国建筑师,人家也羡慕咱们,真是互相羡慕。人家没活干怎么办呀。 ஸஸ美国建筑师现在关注的问题我不太认同,比较形式主义,也包括一些欧洲的建筑师。但荷兰、西班牙的建筑师对城市的关注我觉得有意思,他们分析的方法也特别有意思——对城市的关注带来城市、景观、建筑三位一体,实际上我们很受影响;由分析直接构成设计,我们也非常感兴趣。从建筑观念上说,我们也觉得这两个国家是走在前面的。他们是一个群体,而不是库哈斯一个人。 非常建筑、非常实践 ஸஸ成: 您的设计项目大多是中小型项目,甚至有很多是改造设计项目,每个项目多少都能结合业主的要求,形成对材料运用、空间形式、甚至构造方法的新鲜表达,似乎您很乐意在这种限制要素更多更为复杂的项目中进行建筑设计的新实践,这种状况是您有意为之还是市场迫使? ஸஸ张: 对我来说各种限制都是一样的,建筑难也是难在这儿,这就是建筑本质的挑战。让你随便设计、给你无限的钱是不是就一味能设计好呢,我其实是怀疑的。项目不管大小,本质上都一样。对于建筑师来说,不管是什么样的项目,比如我们现在做的项目,4万多平方米,算个大项目了,真正的挑战在哪里,哪里有意思,其实是建筑师赋予它的,以前做的很多中小项目也是一样。这就是我们做研究必然要带来的,就是对一个工程理解到一个份上——它本来可能没有意思,你把它变得有意思。在中国常常因为一个项目太重要了,管的人也多,出来的效果都不是太理想,你看世纪坛,难道还不重要,出来这么一个建筑还是挺难过的呵。 ஸஸ中国现在有个实际情况就是工程做得很快,谈判很慢,本来时间就不多,可能好几个礼拜都用在谈合同上了,实际做的时间就特紧张,所以我们要把所谓的研究组织得特别快,得很快明确我们研究什么,所谓的策略就在这儿——这项目从哪儿出发。这种组织是内容的组织,而不是其他操作性的组织,我的工作就是把大家的兴趣带起来,让我的同事觉得思考这个问题很有意思,那就开始做了。 成: 古人有说,“一派学问引出一种观点,一种观点引出一方语言”,语言其实是具有个人特征和饱含对世界态度、立场的一种产品,您运用建筑设计语言在一些工程项目中进行了表达,现在您自己愿意用什么样的语言对它们进行描述? ஸஸ张: 建筑语言问题对我们来说是这么一种情况,从刚回国一直做到大概两年前,建筑的形式语言我们没有一个思考的依据,因为这里也是永远含着希望按照中国的一些条件,包括对文化的环境等等来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从文化来说对建筑形式语言的探索,实际上在一定程度是回避的,考虑的问题也挺多,有建造的问题、空间的问题、使用的问题,可在形式语言方面基本都只是进行一个趣味的控制,这跟西方的现代主义建筑有比较类似的一面,可是如果你仔细看我们的房子,又不特别强调有明显的风格的东西,实际上是回避的。因为那种基本上使它具有现代建筑的特点,可也不是按照现代建筑最典型的思路出牌、出招的。过去这两年,慢慢地,我们开始比较清楚一点的是用一些方法对传统的建筑进行一些翻译,可能有很多项目都跟这个发生关系,都能体现这类工作和思考 。 ஸஸ成: 在中国当前的建造速度惯性下,大部分从业建筑师已经很难在一个从容、沉潜的状态开展工作,您的建筑设计实践侧重于哪些方面,或者说,在方案、扩初、施工图设计以及建造实现四大阶段,你的哪些作品产生出合乎您意愿的效果? ஸஸ张: 状态当然是谈不上从容,所以那天有谁一说策略,听上去好像特机会主义,我倒不觉得,正因为时间压力、速度,就得有选择,你怎么做都是策略的问题。策略是,可能在建筑设计的范围里选一个两个点来进攻。侧重哪个阶段,实际上不同的工程是不一样的,有的工程,时间特别紧,像那些改造的、短期的,就得在观念上比较清楚,有些是造价比较高,建造时间也比较长,参与的也可以比较多的,在建造上就可以多下功夫。总的说来,实际上我们做的没有什么好东西,都离我们想达到的一个质量差得挺远。可反过来,最重要的是最关键的那点是否达到了——如果你要做一个南方建筑,它没有变成一个北方建筑,这点就最重要。所以一方面,没有哪个房子特别满意,都觉得不满意;另一方面,有时候说能给自己打个六七十分也挺高兴的了,因为这六七十分里就有主攻的方面。 ஸஸ我们的项目,最不满意的一般都是建造质量。还有,像水关长城的二分宅,大家就说到里面的那个水平受力的叉子不好,我也同意,不好。当然很遗憾,跟结构工程师打交道的时候我们未能提出一个更积极的结构方案,不打叉子他不签字,认为那样一个水平受力是有问题的。如果是现在,有时间、有能力的话,我们建筑师自己就应该去想一些改善水平受力的方法。这里面最滑稽的一件事,是传统的房子为什么不打叉子也行啊,因为传统的木结构可以允许倾斜,不倒就没关系,因为人不会受伤。其实我们那房子也完全可以是这情况,可现在抗震一般都是用钢性抗震的思考方法去对待。 ஸஸ设计不满意的地方也有,像重庆生物试验基地项目里的山墙,因为有错层,剖面关系挺有意思,我们想把剖面关系暴露出来,实际上没能暴露出来而是表现出来,现在回想起来觉得特没意思,就像用建筑愣说故事似的。最后抹的楼板的厚度和白墙的关系根本就不好。 ஸஸ我们在大的构造关系,基本的空间关系、使用关系、建造关系上还比较清楚。一旦清楚了,它的建造质量好坏,也不至于影响到整个工程一无是处。 ஸஸ成: 接设计任务做方案之前,在看到建设场地的时候,是否会因为场地与设计任务的要求发生了第一下的碰撞而在脑海中首先浮现出一个该未来建筑大略的形象,或者它的某些要素,有关空间啊、质量啊、温度色彩啊等等特性。您一般怎么处理直觉与理性经验? 张: 现在场地和旁边的环境呀,常常挺难看,场地本身其实很少能带来刺激,有些自然的环境当然除外。常常倒是我跟业主开会的时候会来想法,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精神会特别集中,第一次会上可能就会想到这个房子应该怎么做,对我来说,因为以前的工作习惯,是关注空间的东西,一个空间关系、空间系列,所以有时谈判、合同一完常常就可以开始工作了。我们的工作特别不一样的,是要定入手点的。我们的理性经验、理性的思考方法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起点,而且特别适合于合作。既然是理性的、说道理,就特别容易沟通,而不是一个人说“我就觉得怎么好,应该怎么样”,说那样的话毫无意义,别人的智慧发挥不出来。当然最后几种不同的意见需要统一,利用自己的权力独裁一把倒是可能的。 ஸஸ成: 在研讨会上,有人提到“非常建筑十年”的“非常”,在于其批判性地参与着中国建设,您能就这方面谈谈吗?后来又有吴钢在表达某个观点时将你们事务所的名称演绎为“从非建筑到常建筑”,您怎么看? ஸஸ张: 批判地参与,它本质的态度就是,任何一个所谓知识分子对市场经济得有一个认识,当你进入市场经济,如果仅仅是生产和消费这么一个机制的参与者,实际上你的工作就没有其他的意义了。其他的意义在于你得比较清醒地考虑生产以外是什么,你并不是不参加生产,盖一大堆房子就是生产。实际上关注建筑本身就构成一种批判,谈学术就构成一种批判。有人觉得现在是奢谈学术。可是你关注了建筑本身,你挣钱少可能,挣钱多也可能,都是批判,并不是你一定苦巴巴的,做大项目你也可以批判。关注建筑本身、做研究我认为都具有批判性,虽然在这样一个生产压力下很难做到。现在学术不是奢谈,是必须谈,否则一大堆垃圾出来你挣钱多少也属于消极参与市场经济。 ஸஸ吴钢这说法,我也知道他的意思,现在很多人认为我们的非常建筑已经很正常了,王澍又说其实吃不准我们到底有多正常,这里面说明两个问题,我们所考虑的问题我认为带有相当普遍性,所以实际上真的“不非常”。如果好多建筑师能分享我们这些关注点,应该对城市和社会都是积极的。可另一方面,因为我们的思想方法,它不是真的能变成一个常规的操作,如果每一个项目都做研究,其实跟一个比较正常的实践还是挺不一样的。下一步我们工作室也不知道能做成什么样,并没有真的比较有组织地控制,而是比较有组织地研究,结果就不太控制,所以就不是很“正常”。总的来说,看自己不太清楚,别人说正常了呢也许是。还有就是,具体工程的事情,哪能知道下一个项目能是什么机会,自己当时的状态和思考能把它带到哪儿,都是很难说的。大家现在还没看到的东西如果看到了,对我们的想法也许又会改变,包括这拨新工程里的东西,对建筑形式探索的新的系列。 ஸஸ有时候上网看看,我就觉得对我们的工作做得多艰苦大家可能比较难想象。当然是两方面,十年前的条件不太一样,还有就是我们的能力实在是有限,全靠愣拼,一天到晚就是想玩了命。现在挺滑稽的一件事是,按说中国在跟国际接轨,我们跟国际接轨好像不是问题,是跟国内接轨老接不上。国外的建筑师难的不一样,他们找个活特别难。我的理解是国外的个人的事务所是有个传统的,大家都知道这个难度,中国建筑师反而不熟悉,会想象我们跟他们所处的情况不一样,其实有什么不一样。真正不一样的是,我们想做的事情不一样,这样我们的难度也不一样。有人说我们像玩票的,因为在探索的那些地方他们不知道我们想得那么苦,以为只是突发奇想,实际上真的是费了很大劲。 ஸஸ说服业主的工作一般人也不了解,以为我们特容易,以为我们说什么业主就听,现在也许好一点,过去十年可不这样,得做多少工作、变着法儿做工作,才让业主知道我们究竟想干什么。有时候根本不是业主被说服,而是业主被感动了,觉得我们特别真诚,觉得就让你们试试得了。特别是审美的差距比较大,但还是会被感动。人嘛。
润唐山庄集合住宅
贝森新文化空间
玻璃洋葱西餐厅
北京大学(青岛)国际学术中心
远洋艺术中心
西南生物工程产业化中间试验基地
分成两半的房子
北京大学青岛会议中心
作品列表
席殊书屋
山语间别墅
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中心
“颠倒办公室”康明斯亚洲总部 |

